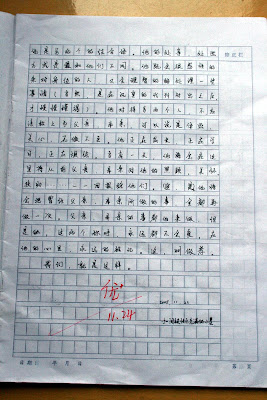話別趙來發﹕溫柔如發
文章日期:2009年1月15日
明報專訊】發仔走了。
知道發仔有病以至入瑪麗住院已有一段日子,但自己竟沒去探過他一次半次,說來慚愧,也更抵打。自己每次想及跑去探他的時候,都總否決這個去探老朋友的衝動。想深一層,自己其實是不想去見去看一個患病的發仔,一個飽受疾病折磨的發仔,一個不健康的發仔。因為一直以來,由二十幾年前我初次認識他的時候開始,發仔在我心目之中都是那麼健康、那麼陽光、那麼瀟灑,我始終都希望將他這個形象以至性格,長留在我自己的回憶當中。
認識發仔的那個年代,大學文化嚮往淳樸及內在優點,幾乎沒有很多人會介意自己的外表,包括我自己在內,所以發仔的出現是具有相當啟發性的,
原來大學生可以如此乾淨,如此溫柔(套用當年另一老友黃碧雲對發仔的「形容詞」),但又可以如此的自然。智慧方面,當年實在理論界次文化界高手如雲,把口大聲細聲怪聲大有人在,但毫無疑問,發仔的智慧是內斂的,溫柔的,文化分析他不會下下都馬克思主義以至階級分析,高Q大棍,但他總會有他的觀點、他的角度,聲線不大,不似癲狗,只像跳脫的小貓,令人舒服。本人不多外遊,但外遊經歷當中,最有趣最快樂的一次就是當年和發仔及大樂(中大呂大樂教授)在所有人未發現日本、未發現東京之前和他倆把臂同遊過東瀛七天。通過發仔我學會了欣賞京都、欣賞櫻花、欣賞小小一口井,小小一塊石頭,正如我說過發仔不是大口徑的階級分析一模一樣,他的分析及觀點都是微觀點,不會一筆勾銷事物的可觀性及複雜性,進入了微觀世界,才是精華所在。
所以,如無意外,發仔的一生一定是多姿多彩的,當所有人都習慣用還原主義、乜乜主義、物物主義去分析事物時,他應會堅持將「事物」「還原」至「事物」本身,品味物品,品味人生。發仔這次去了,我遺憾的是沒有機會和他談生論死,但我十分肯定,
發仔走之前,一定又已經洞察生死,理解人生,去得灑脫,去得自然,再見吧,趙來發!![文.邵國華]
話別趙來發﹕趙教父夠沉默未?
文章日期:2009年1月15日
【明報專訊】如果香港真的有什麼「新紀元『運動』」,趙來發應該是眾望所歸的開山祖師。
早於一九八○年代末期,他已經在不同的崗位上推廣素食、環保,以及各式各樣玄學和保健養生的思想與功法。
明白「新紀元」的人都會同意,這一回事不是一種宗教、不是一種流行風氣、不是一種意識形態、不是一種運動——雖然表面上好像都全是。說它是一個社會轉化的過程才最貼切。
而它最大的特色正是沒有教規、沒有中央組織、沒有教主或僧侶、沒有欽定的經典、沒有所謂會籍身分,甚至連半套公認的思想哲理亦欠奉。所以,其實沒有人在傳「教」,亦無權威。有的,無非是有意無意覺醒了而改變思想行為的一股大力量。人人都是未經按立的司祭和宣道家,大家的行動一天到晚無形中在證道。
刻意地不刻意行慈悲
趙來發的恩師潘嘉大師(Poonjaji)講過這個故事令阿祥最震撼:某位高人行旅途中倦極在樹林裏倚樹小睡,一覺醒來竟然發現四周圍滿了人,他們全體行禮朝拜,再三感謝大師開示,咸稱獲益匪淺。高人說自己什麼都沒有做過,只是在午睡,他們卻說感應到他無言之中令人開悟,因此呼朋引伴爭相到來收料。
潘嘉大師力主什麼都不要(刻意)做、什麼都不要(刻意)講,只要心靜、搭通天地線,那麼上天自然就會用意想不到的方法,如此這般完成你在世上受到安排的工作。此所以阿發的遺世巨著正是叫做《讓沉默說法》。本地綠林大俠阿祥總算認識不少,敢稱想不出有誰對於「新紀元」思想了解透徹而同時掌握各種「新紀元」玩意技藝那麼精湛,近廿年來孜孜不倦又講又寫又編,好像無數的事做不完,甚至力不從心。
正是這種力不從心令他的身體堅決要提早收工,有朋友這樣看。阿祥倒認為阿發一方面好像未遵師命,隨遇而安;說到底反而深得其真傳:潘嘉大師有個精彩的比喻說,尾車開了,車站就該關上(是訓示弟子在他死後勿搞組織?)。做人可以做得到什麼,就輕鬆開心去做;時候一到就要毅然放下,輕鬆開心上路,繼續享受下一程的風光好了。
阿祥自己和身邊不少人受過趙來發的指導、感染,走上茹素、靜心、能量療癒之綠色大道,加入了「新紀元」的洪流。從俗世眼光而論,阿發也許未算立下轟轟烈烈的功業,然而事實上他「沉默說法」的綠化 人心影響力,恐怕是本地文化發展不容抹煞的一章。
「在茫茫冥冥的宇宙天地間,一股啟明導盲的力量,徐徐流動。是雷電劃破黑夜長空,是涼風吹過烈火地獄,是喧鬧塵世的一刻清靜。」他這樣描述自己跟靈性老師親近接觸的經驗。這也是多年來我與跟他在一個復一個綠色團體共事的經驗!
[文.周兆祥]
重要一課文章日期:2009年1月15日
【明報專訊】上周四,從同事口中得悉,昔日上司趙來發走了。
因為發哥,我回歸前加入《明報》。那時的副刊,個個都是阿哥阿姐。除了明星記者,還有幾個年少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記者,我是其一。當時,我們什麼版面都要做,時裝、消費、文化、人物訪問、專題、娛樂,甚至碧姬去派對,都是在發發(對,那時我們喜歡這樣喚發哥)的領導下完成的。那是一段快樂時光,同事們都是性格巨星,全因發哥的魅力聚在一起,產生很有趣的化學作用。
上司有很多類型,唯獨發哥是不能歸類。他可以是精神領袖,又可以是文采飛揚的才子,更可以是心靈導師。曾經,在我找不到自己、感到沒有力氣向前走的時候,找當時已離職的發哥,藉故找他看手相,實情是找他作心理輔導。我從沒遇過一名可以跟你分享秘密的上司,將來都應該沒有了。
發哥有很多值得我輩學習的東西,像處事不慌不忙,有胸襟有抱負,但又洞悉世情的態度,很多人窮畢生之力都做不到。我難忘他跟大家打招呼時最愛舉的V字手勢。三年前,他入院做檢查,跟舊同事一起探望,找了位卻不見人。不一會,看見躺在病的發哥被護士推回來。儘管他瘦了一圈,仍神氣地向我們高舉V字。那一刻,我頓時語塞,不懂說話了。
知道發哥病重的時候,想探望但又不知應該說什麼。我眼淺,怕一見就即時崩潰。能做的就是看他的blog,為他打氣。
他在blog上寫求醫過程,病中承受的痛苦,坦率得令人害怕,他反過來安慰大家不要怕。或者,發哥要讓我們知道,所有人都有離開的一天,學習怎樣豁達的面對死亡,才是人生重要一課。[Clara Chan]
人群外圍的靜少年文章日期:2009年1月15日
【明報專訊】不少人問我寫了這專欄多久,我忘了,大概十年吧!
緣於跟趙來發午膳,我吃午餐,他茹素,自言在家吃過早飯,只要一杯咖啡。
我不知道他當年在《明報》的職位,談過公事以後,問他可否寫專欄,他一怔,說回去想想。幾天後,編輯給我電話,開這專欄。
我感謝他,但從來沒說。跟他只有一面之緣,我自顧自吃了整份午餐,準備結帳,他隨即多要一杯咖啡,搶了埋單,那餐飯倒直接跟他道謝了。
數年前,從傳媒得悉他患癌,一直希望有奇蹟出現,可惜沒有。
曾編幾本香港短篇小說選,有本選了他的小說,因為他寫得好,他的個人簡介更寫來坦然,
收筆是:「寫作這個故事,才發覺十幾年前那個只愛冷眼一旁的少年,原來還未成長,就站在我的身後,瞪眼看我。」在他患病期間,不想打擾,如果那時寫感謝他的文章,更像認定他時日無多,我無意如此。我只是偶爾得他幫助的過路人,或者,他根本不在乎路人感謝與否。
也許,趙來發仍是那個只愛冷眼一旁的少年,站在一旁,細看人間滄桑——這篇題目是他在選集自我介紹的命題。
[關麗珊 http://www.voy.com/144163/]